郭鹏:中国古代诗学内在演进理路与基础学理
[原标题:由学诗而诗学——中国古代诗学内在演进理路与基础学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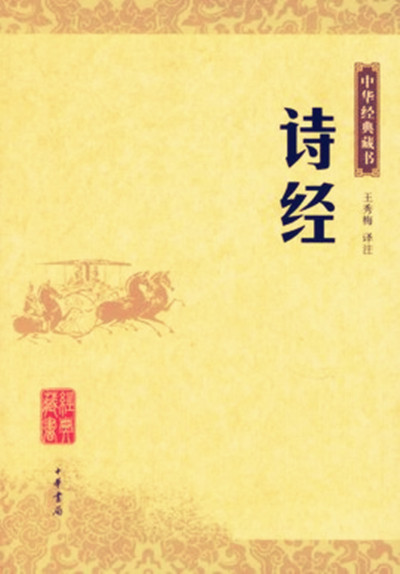
《诗经》
古代诗学的内在演进理路表现为由“学诗”到“诗学”的逐渐过渡。“学诗”的主观意图与实际内容在于通过有目的的研习与探究去掌握诗歌的基本特点和创作规律。古代“诗学”由“学诗”移衍而来,并沾溉了较为一贯的对学习诗歌创作与鉴赏批评的实践指导与要领传授色彩。古代诗学的基本特点与其由“学诗”萌孽而来的学理渊源直接相关。因此,对诗歌创作的基本意旨进行强调,对如何汲取经验、提高创作能力和批评水准进行传授指导,遂成为我们现在所谓的古代诗学的基础学理。
关于“学诗”
“学诗”原系学习《诗经》,所学习的范围既有义理方面的“思无邪”(《论语·为政》),也有情感方面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论语·季氏》载孔子告诉其子孔鲤云:“不学诗,无以言”,其“学诗”,盖指学习“诗三百”中称诗以谕志的交流方式以增进言语交流能力。至于“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之说(《论语·阳货》),则可视为孔子对于“学诗”的包举宏纤式的明确指授。孔子所提出的“兴”、“观”、“群”、“怨”之说,其意旨便在于强调诗对于谐洽人我,构建和谐有序的人文社会所起到的实践作用。至于“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则是出于对士君子博物洽闻的素养方面的要求。孔子对“学诗”的阐释,基本奠定了汉儒“学诗”的意义范围。可见,孔子用到的“学诗”,含义十分宽泛,是其“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的系统教育思维的重要环节。
从学习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艺术的创作技能角度考察,汉代之前实际上也已经有了专门研习的实例。屈原所创立的“楚辞体”诗歌,后来又有宋玉、唐勒、景差以致贾谊等人的效法沿袭,其实就是在学习“楚辞体”诗歌的创作经验和技能。西汉末期扬雄就颇能钻研并效法前人以实施自己的创作行为。《汉书·扬雄传》说扬雄模仿《周易》作了《太玄》,模仿《论语》作了《法言》,模仿《仓颉》作了《训纂》,模仿《虞箴》作了《州箴》,还分别模仿了屈原和司马相如的作品,其目的则是“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除了模拟撰写一些学术性的著作外,扬雄对屈原和司马相如的辞赋类作品的仿作实际就是“学诗”的一种实践。后世文人在学习前人时所说的“入门须正,立志须高”、“工夫须从上做下,不可从下做上” (《沧浪诗话·诗辨》)等诗学观点的思想来源,就是扬雄这种仿作式的“学诗”实践。
及至汉武帝时期儒学定于一尊,《诗经》遂成为经学家研习的主要对象。汉代人所用到的“学诗”,一般指学习《诗经》而言,主要是指对《诗经》所含政教信息及其意义的细致参究,其中也包括对相关的名物、典章和制度的研究。“学诗”借着经学总体风气的助推作用,其含义便延展到有关词语训示和典章名物的考证方面。
随着“文学自觉”和诗歌本身的发展,“学诗”开始有了明确的学习作诗的含义,“诗学”的含义随即发生变化,逐渐指涉关于诗歌的认识和创作能力的培养等意旨。齐梁时期的《文心雕龙》和《诗品》均有鲜明的指导如何学习鉴赏甚至是进行创作的意味。唐宋时期是“学诗”之意从《诗经》学意义向诗歌创作实践过渡的关键时期,而“诗学”也成为实践性极强的指导学者掌握诗歌创作和批评鉴赏的思路以及方法的“专门之学”。由“学诗”而“诗学”再到形成诗学传统的发展轨迹背后,隐含着决定我国古代诗学传统之基本特色的重要内理。
关于“诗学”
由“学诗”萌孽出的“诗学”,至唐宋时期,已经具有了专门的含义,盖指对诗歌创作规律的把握和创作时应予以贯彻的一系列相关问题,包括诗歌应该具有怎样的审美特征等方面的理论认识。到这一时期,我国古代“诗学”重实践指授的民族特征已然初步成型。唐人已经屡屡使用“诗学”来表示对诗歌创作以及审美内蕴的相关认识,其含义早已经不是指经学范畴的《诗经》学了。宋代学者在使用“诗学”一词时,就专指包括诗歌创作的立意造言、遣词用语和章法安排等专门化的诗学理论问题。从中晚唐的诗格、诗法类著作的勃兴也能够看出,在当时已经以专门化的“诗学”理论或是规则矩矱来指导诗歌创作了。虽说对诗歌主旨的阐述还能看出《诗经》学的影响,但这些理论著作的主体内容已经是诗学理论内在的诸多问题了。宋代江西诗派也好,江湖诗派也罢,其理论关注的重心,依然在于如何指导后学去学习前人。这种诗学观点,显然缘自对“学诗”问题的深入考量。尤其是严羽提出“以汉魏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沧浪诗话·诗辨》)以后,迭经戴表元的“宗唐得古”与明代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推毂,古代诗学关注如何“学诗”的意旨就十分鲜明了。
在“诗学”由“学诗”萌孽并推衍的过程中,尤其应该关注金元之际的元好问。元好问多次运用“诗学”来表述其以诗歌的创作和对相关理论的把握为“专门之学”的意思。他在《杨叔能小亨集引》中说:“贞佑南渡后,诗学大行。初亦未知适从。溪南辛敬之、淄川杨叔能以唐人为指归……知本焉尔矣!何谓本?诚是也……故由心而诚,由诚而言,由言而诗也,三者相为一。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发乎迩而见乎远。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虽小夫、贱妇、孤臣、孽子之感讽,皆可以厚人伦,美教化,无他道也。故曰不诚无物。夫惟不诚,故言无所主,心口别为二物,物我邈其千里。漠然而往,悠然而来,人之听之,若春风之过马耳。其欲动天地,感神鬼,难矣!”可见,在元好问的观念中,“诗学”就是研习古人作诗的“专门之学”。元好问认为《诗经》和唐诗为诗学正统,他在阐释“不诚无物”的诗学意旨时,将话题自然转向了诗歌在表达作者心志时的“心”与“口”的问题。这样,就把后人关于诗歌创作的宗旨、趣味和语言运用等问题纳入到了研习参究的范围之内,并统摄于《诗经》、唐诗的统绪之中。元好问多次使用“诗学”、“以诗为专门之学”来表述他对某些诗人具有理论素养的认识。可见,“诗学”在这一时期,已具有类似我们现在所说的,以诗歌为主要文体的关于文学艺术的一系列理论观点的内涵。
从古代诗学的发展来看,承续《诗》《骚》传统,秉受风雅比兴的抒情写志主旨,力矫“讹滥”,扫除“浮伪”,或师唐,或法宋,成为诗学的理论重心;构建并排布意象群以容纳感情,追求“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美学意蕴成为诗学的审美追求。或是熔铸学力,致敬古贤,旨在做到“无一字无来处”;或是直抒性灵,做到“我手写我口”;或是要求写出“诗趣”,表现“鸢飞鱼跃”的勃勃生机;或是规行矩步,严示格法,生怕诗歌创作坠入“野狐外道”……凡斯种种,成就了诗学的缤纷色调与五彩光澜。而这些构成古代诗学理论堂奥的“专门之学”,都蕴含着源自于“学诗”的内在理路与外在关切。
“学诗”由学习与研治《诗经》发端,在后世逐渐移衍为学习前人创作经验、掌握创作技巧、提升鉴赏批评能力的“专门之学”。于是就有了“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的教诲;就有了“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的告语;也有了“入门须正,立志须高”的指示和“为诗必以肌理为准”的主张:或是指引门径,安排推进进程;或是强调学力,认为借此可以“夺胎换骨”;或是标橥“兴趣”、“神韵”,力推“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审美境界;或是主张师法唐诗;或是要求瓣香宋人……古代诗学中大量的诗格、诗法和诗话著作中,充盈着对后学的谆谆告诫,洋溢着对诗歌发展的忳诚关切。“学诗”生发出许多诗学问题,不只是古代诗学的先期形态,也是催化剂和理论繁育的皋壤;“诗学”则绍续着“学诗”的基本内涵与学理框架,形成了既可学而能,又可用以指导后学的特色与风貌。古代诗人代兴不辍,古代诗统延续至今,没有传统诗学的实践性指导内理是难以想象的。
由“学诗”而“诗学”是我国古代诗学甚至是文学理论的内在发展与演进轨迹,也是古代诗学学理的根柢与基础。它绵延至今,既形成了民族化的诗学理论传统,又规约着未来,引领者诗学今后的走向。我国古代诗学重实践、可授受,不务空泛,不钦虚无缥缈的传统诗学特质由此生成并逐渐壮大。在我们探寻古代诗学的内在学理与发展脉络的时候,找准关键,才能提纲挈领。(作者单位:山西大学文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