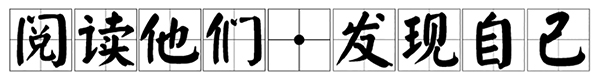总工告诉你,港珠澳大桥建造有多难?丨观注·林鸣

百字观:这座大桥建了14年,比连续33次考上清华都难
10月23日上午,世界最长跨海大桥——港珠澳大桥正式开通。作为媒体眼中的“新世界7大奇迹之一”,横跨伶仃洋,硬生生将香港、珠海和澳门三地连接在一起的这座大桥创下了多个世界纪录:最长跨海大桥(55公里)、最长钢铁大桥(15公里的全钢结构)、最长海底隧道(6.7公里)、最大沉管隧道、最精准深海之吻……总之,这座预计使用寿命超过120年的大桥,综合技术难度最高!当然,从2004年成立前期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到今年(2018年)建成,这座建设了14年的“超级工程”,一路走来,也遇到了很多超乎想象的困难与挑战。对此,港珠澳大桥岛隧总工林鸣称:港珠澳大桥建造有多难?就像是连续33次考上清华的感觉!

善德注(一):面对老外的狮子大开口,他成就了中国史无前例的超级工程!
时间拨回到2005年,那一年建设港珠澳大桥计划刚刚提出,但现实情况是,在沉管隧道领域,中国的技术还无法望及国际水平。
如此情况下,国外媒体都特别关注港珠澳大桥,其实就是因为一个字:“难”。工程体量之巨大,建设条件之复杂,是以往世界同类工程都没有遇到的。
在当时,全国江河沉管隧道总长不超过4000米,而在此基础上,光建立一个长5664米的外海沉管隧道,其费用之高、难度之大、风险之大,就吓退了无数前来应标的公司!
可这个重担,偏偏就落在了工程师林鸣身上。得到通知后,他一宿未眠。他知道,要建造港珠澳大桥,必须要突破三个难点:首先,港珠澳大桥需要建造一个外海沉管隧道,但在港珠澳大桥之前,全中国的沉管隧道工程加起来不到4公里。其次,这是我国第一次在外海环境下建沉管隧道,可以说是从零开始,从零跨越。最后,技术力量不够,钱也不够。
2007年,林鸣带着工程师们,去全球各地桥梁工程考察,当时世界只有2条超过3公里的隧道,一个是欧洲的厄勒海峡隧道,还有一个是韩国釜山的巨加跨海大桥。
当林鸣带着团队来到釜山时,就向接待方诚恳地提出,能不能到附近去看一看他们的装备,却被拒绝了。无奈之下,考察团只有来到大概离工程300米左右的海面上,开了个船过了一下,用卡片机拍了几张照片。
从釜山回来后,林鸣更加坚定一个决心:港珠澳大桥一定要找到世界上最好的,有外海沉管安装经验的公司来合作。
于是,他们找了当时世界上最好的一家荷兰公司合作,人家开了个天价:1.5亿欧元!当时约合15亿人民币。
谈判过程异常艰难,最后一次谈判时,林鸣妥协说:3亿人民币,一个框架,能不能提供给我们最重要的、风险最大的这部分的支持。
但是,荷兰人戏谑地笑了笑:“我给你们唱首歌,唱首祈祷歌!”
与荷兰人谈崩后,林鸣带领团队自主攻关,解决了多个世界难题,最终实现了工程设计零借鉴、安装零失误。林鸣说:“我们所建设的不仅仅是香港回归后的世纪工程,更是大国的经济宏图,我们一定要立足自主创新!”
在几乎空白的基础上进行自主研发,林鸣和他的团队面对的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在伶仃洋水下50米深处,安装成长达6.7公里的海底通道,需要将33节,每节重达8万吨,长达180米,宽约38米,高11.4米的钢筋混凝土管,完成高精度的海底对接。这一项施工的技术难度,堪比“海底穿针”。

2017年5月2日早晨日出时分,最后一节沉管的安装,终于完成了,船上一片欢呼,世界最大的沉管隧道——港珠澳大桥沉管隧道顺利合龙。
中国乃至世界各大媒体,都在为这项超级工程的完美落幕欢呼,而此时的林鸣,却在焦急地等待最后的偏差测量结果。
偏差16公分,这于水密工程而言算是成功。而中国的设计师、工程师、包括瑞士、荷兰的顾问……大多数人也认为滴水不漏,没问题。
但林鸣说:不行,重来!
茫茫大海,暗流汹涌,把一个已经固定在深海基槽内、重达6000多吨的大家伙重新吊起、重新对接,一旦出现差错,后果不堪设想。
“算了吧。”
“还是算了吧!”
几乎所有人都想说服林鸣罢手。
这时,林鸣内心出现一个声音:如果不调整的话,会是自己职业生涯和人生里,一个永远的偏差。”
他把已经买了机票准备回家的外方工程师,又“抓”了回来。经过42小时的重新精调,偏差从16公分降到了不到2.5毫米!缩小了几十倍的差距!
那一夜,他睡了10多年来的第一个安稳觉。

善德注(二):人生只有一个标准,只有一种态度
作为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项目总经理、总工程师,面对工程创造的一个又一个“第一”,他表示:“不是说超级工程就超级态度,一般工程就一般态度。人生只有一个标准,只有一种态度,那就是不断奔跑,把每件事做好。”这是人生信念的定格。
大桥建设期间,来港珠澳大桥考察的国内外专家不计其数。总有人问,为什么中国能在一片空白的情况下建设全球最长的跨海大桥?林鸣说:“即使我们的起步是0,我们往前走一步就会变成1。”从零到一,看起来只是一步,但却是多少汗水、多少挑战、多少个不眠之夜成就的一步。一次午饭后,林鸣带领团队就项目一个工程环节的可行性进行研讨。讨论激烈,却一直没有达成会议研讨的成果目标。林鸣的习惯大家再熟悉不过——决不开没有结果的会议,决不做没有成效的讨论。当讨论终于柳暗花明,林鸣宣布散会,叮嘱大家吃点夜宵、早点休息之时,不想大家面面相觑,无奈地笑了起来:“哪还有夜宵?该吃早饭了!” 拉开会议室的厚窗帘,阳光洒满了整个房间,已是第二天清晨六点多。
曾有记者问:“建设过程中,您什么时候最难?”
林鸣说:“哪有什么最难,每天都很难。我的工作,就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不断突破难点。”
岛隧项目副总工、林鸣的“弟子”之一高纪兵说,跟着师父干,就一个字——“累”,但是累得值得,因为进步特别大。“跟他干下来,什么工程都能干。”
对此,林鸣表示,干大项目,必须勇于担当、敢于牺牲。牺牲“小我”,才能成就“大我”。他还说:“人生在创造的时候很艰难,但不断奔跑的人生才是最充实的人生。桥的价值在于承载,而人的价值在于担当。我一辈子都在修桥,造好桥、做好事就是自己的人生价值。”(图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