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勤:为什么说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
2019年2月24日,也就是昨天,李学勤先生因病逝世。
李学勤,一位一生都在奋力找寻中华文明起源痕迹的历史学家,一位旗帜鲜明地提倡“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走出疑古时代”的学术巨子。自1995年主持夏商周断代工程以来,他的学术方法和研究报告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巨大争议,所以,作为一种学术思潮的代表人物,“李学勤”已经成为一座史学地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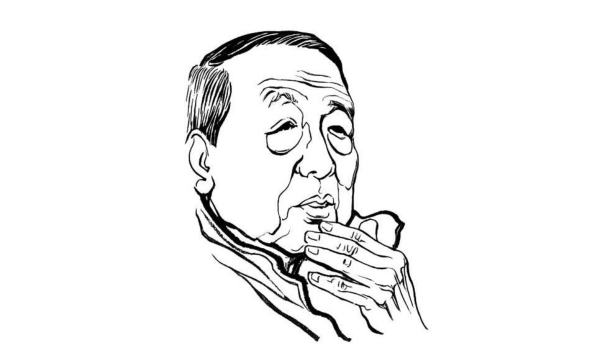
如今,斯人已去,回听他那句:“中国古代文明史,曾因西方偏见而被刻意贬低!”当作何感呢?
有道是:“清者自清浊自浊,是非经过莫评说。”关于李学勤先生之学品高下,不妨看看他眼中的中国古代文明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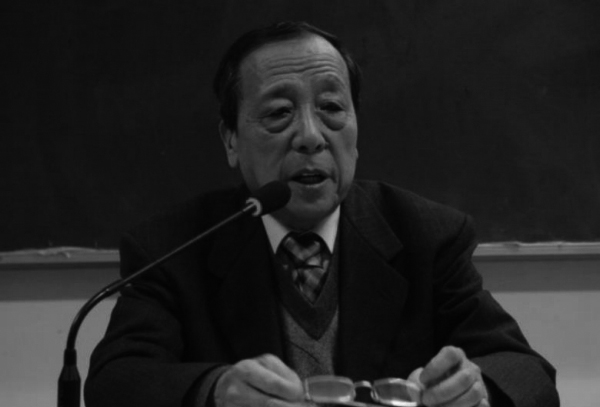
为什么说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
李学勤:大家知道,我们国家有一套正史:二十四史,第一部是《史记》。《史记》一开始是《五帝本纪》,《五帝本纪》是从炎帝、黄帝开始的。炎帝、黄帝是在什么时代?按照在中国历代的史书记载来推算,离我们今天大约5000年左右。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辛亥革命的时候,很多革命的先驱者,他们为了不用清朝光绪、宣统这样的年号,就用黄帝纪元。黄帝纪元不能算得很准确,大致上有几种不同的算法,但都在1911年以前的4700年左右,再加上前面的炎帝,所以炎黄时期就距我们今天大约5000年的时间。我们常常说我们是“炎黄子孙”。炎黄子孙这个词和5000年的文明史是一回事。因为我们是炎黄子孙,所以有5000年的文明史。大家如果到陕西的黄帝陵去看,那儿有很大的一块匾,匾上写着“人文初祖”。人文初祖,就是文明起源的意思。5000年的文明史就是这么来的。

中国文明的起源到底在什么时代?
李学勤:大家可能会看一些外国学者的书,那些书上,公认的中国文明起源是从商代开始,如果是这样,就是公元前1600年。甚至于有人说是从发现甲骨文的商代后期开始,那么就要从盘庚迁殷来算。大家都知道,商王盘庚把首都从奄迁到了殷,也就是今天河南安阳的殷墟,此后商朝再没有迁过都,盘庚迁殷大约发生在公元前1300年,也就是说我们的文明是从公元前1300年开始的。但是,现在我们看起来这种说法不太公正。因为不但古书里的记载比这悠长得多,而且考古学的客观考察也表明商代已有很发达的青铜文化,它的文明已有非常大的发展了。以文字为例,我们现在知道甲骨文里有多少不同的字呢?大约四千到五千之间,而这四千多个字还不是当时文字的全部。甲骨文是商王和贵族用于占卜的,内容不可能包括当时生活和文化现象的各个方面,因此它不可能把所有的字都包括在内,今天我们任何方面的一本书也不可能把所有的字都包括在内,除了字典。所以当时的字一定要在五千个以上。从这一点,大家都可以体会到商代绝对不是一种很原始的文明,文明的起源要比它早得多。如果,再加上夏代也不过就是再往前推进四百多年,还未必是我们文明的起源,还要再往上推,估计说五千年文明史是有一定根据的。

有争议的“夏朝”真的存在吗?
李学勤:大家知道,甲骨文的时代是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到11世纪),甲骨文的发现使当时的学术界大为震惊。当时很多人怀疑中国的古史,说中国哪有5000年的文明史啊,都是史书上的神话记载。夏商这些朝代到底是不是存在,并没有明确证据。而甲骨文的发现,至少把商代的历史存在完全确定,没有人再敢否认。特别是王国维对于甲骨文的研究,确定了商朝的世系,成为当时震惊世界的一件事。至于夏代是否存在?作为考古学界探寻多年的重大问题,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就已经有了考古证据。那时,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徐炳昶先生带领一批学者到传说中夏的地区进行调查,在他们的调查当中确定了一个重要遗址,就是偃师二里头。经过多年的发掘和调查,对二里头的面积、内涵都比较清楚了,它符合文明的条件。二里头有大型宫殿,还有很多的墓葬,出土的青铜器、玉器、陶器上刻着可能是文字的符号,已经是一个文明社会了。它的时代、地理位置和我们文献记载的夏相吻合,多数学者同意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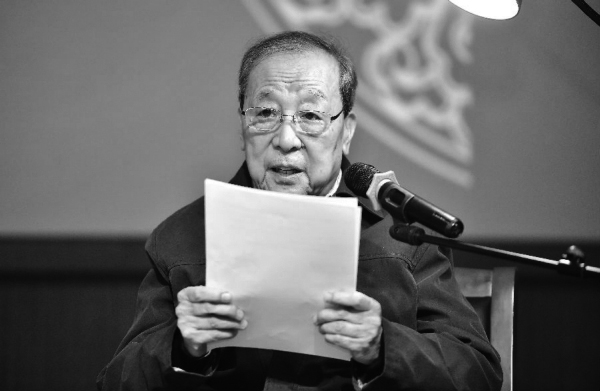
如何看待“夏商周”之前的中华文明史?
李学勤:大家在报刊上或许已经注意到一个重要遗址,就是山西襄汾的陶寺。陶寺遗址的时代又比二里头早,它属于考古学上龙山文化的晚期,根据现在测定的材料,其时代大概是从公元前2600年到公元前2200年,早于夏代。这个遗址有城,城的面积是中原地区龙山文化城址里面最大的。它有城墙、有宫殿。与此相配合,它还有大量的墓葬,其中有些较大的墓出土了很多令人惊奇的东西,最引人注意的是礼器,反映当时的礼乐制度,是文明社会的产物。比如礼器中的磬,和后来的很类似,是三角形的,挂起来可以奏乐;还有鼓,用陶土烧成圆筒形,上面用鳄鱼皮覆盖,也可以敲击。更重要的是,陶寺最近一项很重要的发现,就是有一个“观象台”,这个建筑分为三层,最里面的一层有夯土柱的遗迹,排列紧密,柱与柱之间有缝。在2003年冬至那一天,发现在一个缝里面正好看见日出。大家知道地球公转在三四千年的时间里没有很大的变化。后来在其他节气还有一些观测。如果“观象台”这一点能够确定的话,将是天文考古学上的重大发现,和古书《尧典》里的观象授时是很适合的。《尧典》一项主要的内容就是观测天象,确定历法。据说当时有一年366天的历法,有闰月。尧的年代正与陶寺遗址相当,传说中的尧都平阳正在襄汾附近。

以上,便是从《李学勤谈中国文明》《李学勤:考古学与中国古代文明》等演讲文字稿中摘录的,李学勤关于中国古代文明史的论述。相信读完此文,回望斯人,仰瞻其“忠于信史,耿介敢言”之学品、人品,很多人都会生出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发出的感叹:“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
(来源:中华善德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