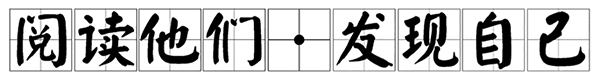君与臣的磨合(三)丨《小张说管仲》专栏之十七
小白沟中学匹夫,相扶霸业并昆吾。
春秋百代留遗迹,堂阜千年入壮图。
福祸塞翁疑失马,险危蒙庆梦啼乌。
只因鲍叔吹嘘力,管氏何须待价沽。
这是明代诗人公跻奎游览堂阜管仲脱囚遗迹,有感而发的一首诗。诗中,“小白沟中学匹夫”一句,说的是姜小白不计私仇任贤者,是能曲能伸的豪杰;“管氏何须待价沽”一句,说的是管仲遭遇不公不自弃,是看淡荣辱高士。
豪杰,勇有余而谋不足;高士,才有余而力不济;当他们相遇,面对面谈论天下时,会发生什么样的争执呢?
公元前685年秋,在姜小白的极大荣遇中,管仲跟着姜小白走上了在齐国边境临时搭建的拜相台,开始了长达三天三夜的对话。
三杯酒过后,姜小白指着案上残羹说:自我的大哥登基做齐王,十三年来,齐国已经由强盛转为极衰!现在脏官恶霸、作恶行奸的人个个锦衣玉食,而平民善士、良吏好兵却人人受苦受穷。战马都是游车用过的老马,战士的给养都是侍妾吃过的剩余;国家庆典,走在前面的不是文武大臣,而是奇淫技巧之辈;国家奖罚,上台的不是实干家,而是善钻营之徒。这样下去,我真担心齐国的宗庙、社稷会沦落到没人打扫的灭国之境。先生啊,我该怎么办?
管仲说:我们的先人已经做出示范了,您也知道,不过是惩恶扬善、选能用贤。
姜小白问:具体说说,都有什么?
管仲说:国分为三,鄙划为五,秉归为六。国之三,就是将百姓划分成工商、士农、直属三个乡,将军士划分成振远、守边、治安三个军,将官员分为施政、监督、荐察三个族。鄙之五,就是以五家为一轨,设轨长;以五百轨为一乡,乡设良人;以五乡为一属,设大夫。秉之六,就是杀、生、贵、贱、贫、富,这是管理“国之三”“鄙之五”的关键,就好像饭锅的把柄。
姜小白听得有些困倦,又好像没听太懂,愣愣地看着管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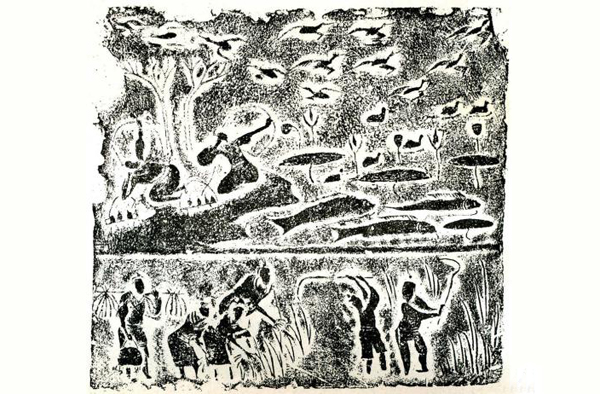
管仲又说:士农工商,国之四民,是国之柱石,不可杂居。
姜小白听完一惊,问:按先生这个排序,那就是读书人排第一,农民排第二,工人排第三,商人排最末。是这样吗?
齐国地贫,一向重视工商,姜小白这么问,自然在管仲的意料之中。见姜小白提起了兴趣,管仲说:士不单指学士,也指军士、义士、隐士;农也不单指耕种者,还包括研究农业者、管理农业者;至于工、商,亦不纯指做工之人、经商之辈。这四类国民,只会根据具体时世变换,做轻重缓急之调,并无高低贵贱之论。
姜小白听完,又恢复了散漫不羁的样子,边饮酒边问:四民分业,有什么好处吗?
管仲说:在全国划定若干地方,让商人相聚而居。他们平常观察年景丰欠,预判市场物价,然后赶牛驾马,买东卖西。他们的子弟整天听这些事,看这些事,不学而自会;慢慢地,我国的商人会因此越来越多,经济也会因此越来越好。
姜小白问:商人聚居,利益面前,不会发生争斗吗?如果他们相互结党,囤积居奇,哄抬物价,为祸百姓怎么办?
管仲指了指窗边的树,说:林有败木,伐之林更盛;树有乱枝,铲之树更直。
管仲继续又讲了工、农、士相聚而居的道理,最后说:四民虽无贵贱,但农是根本,万不可失。他们常年耕地观天,那怕讲不出来,也已深通大道与天时,不然,我们的祖先为什么要敬农而爱农呢!
姜小白开始信服管仲,内心不再唯商是重,问:能不能再给我分析一下。
管仲又指了指窗边的树,说:君如大树,士为阳光,商是风,工是水,农是土。
听完深有感触的姜小白,叹道:树缺了光合、风吹、水养,不会立刻死。而少了土,将无处生矣!
他们君臣谈了三天三夜后,姜小白拉着管仲的手,要正式拜相。将上祭台,管仲回身问道:我若为相,或许会按土地的肥瘠不同而差别征收租税,或许会遗弃一些旧臣,或许会划定伐木、捕鱼的起禁时间,或许会因为农民耕收而阻止您出游、打猎。您能接受吗?
姜小白问:我之志,在于修政以干时(定时会盟诸侯)于天下。您能帮我实现吗?
管仲说:守爱民之道,就可以实现。
姜小白问:什么是爱民之道?
管仲说:公修公族,家修家族,使相连以事,相及以禄,则民相亲矣。放旧罪,修旧宗,立无后,则民殖矣。省刑罚,薄赋敛,则民富矣。乡建贤士,使教于国,则民有礼矣。出令不改,则民正矣。此爱民之道也。
姜小白又问:这样确实可以让四民富贵、安乐。可人民富裕又团结之后,他们还会听我的吗?
管仲说:任才尊贤,则民心悦;加刑无苛,则民怨绝。百姓怎会不听?(系列文章《小张说管仲》之十七 来源:中华善德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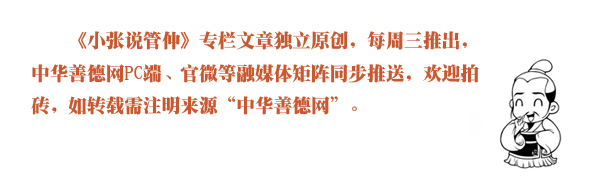
下期提要:
在管仲的建议下,姜小白同意齐国出兵救谭,很快就取得了完胜。只是,最后姜小白并没有重建谭国,而是以“谭无礼”为名,吞并了谭国。
管仲苦劝:得一而失众,你再想想吧。有土之君,不勤于兵,不忌于辱,不辅其过,则社稷安。勤于兵,忌于辱,辅其过,则社稷危啊!
走出齐王国,管仲仰天长叹:看来,齐国称霸安天下的日期,又要推迟了。